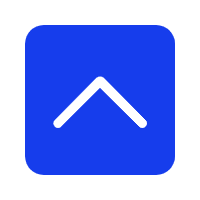邢丽菊:“朝鲜后期儒学的‘心学化倾向’”,《世界哲学》🦇,2014年第4期👱🏽。
内容提要:
18—19世纪的朝鲜后期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心学化倾向”🚵🏿♀️。畿湖学派学者巍岩李柬(1677—1737)和鹿门任圣周(1711—1788)在“心是气”的学派宗旨基础上推导出了“心性一致”。巍岩认为“心是气”的气是湛一清虚的本然之气🤽🏽♀️,本然之心由此纯善的本然之气构成,故心性一致。鹿门继承了这种“湛一之气”🍝🤘,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理气一致,心性同实”。岭南学派学者寒洲李震相(1818—1851)在朱子和退溪“心合理气”的理论基础上推导出“心即理”👲,并以“心为太极”为论据指出,本心就是天理🍹。虽然他们三者都在性理学的术语和逻辑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学问体系👩🏼⚕️,但均不同程度的体现出了一种心学化倾向,由此也反映出朝鲜后期儒学内在的“求心性”特征。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思想背景紧密相关🛀🏼。
18世纪的朝鲜社会已经开始实施荡平政治,下层民力量得到了迅速增长。基于朝鲜小中华主义思想而产生的真景文化也在此时逐渐进入兴盛期🛍️。进入19世纪🛀🏼,朝鲜开始受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侵略的困扰,被动的走上了从属的👨🦱🪚、被扭曲的“西势东渐”之路🍒,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面对国内各种势力的对比分化💂、国外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明冲击🆙,朝鲜士人开始展开不同程度的应对。于是,作为“身之主”的“心”便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巍岩和鹿门的学说赋予了心在价值论上的绝对含义,寒洲的“心即理”则突出强调心的主宰性与准则性之含义。
思想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体🙆🏼♂️。朝鲜时期的儒学作为国家的统治理念和指导思想,无疑承担着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使命感和实践性。因此,18—19世纪朝鲜儒学内部的心学化倾向也可以视为在这种强大的实践推动下自发产生的一种学问倾向🔠。